我无意中看到了Chan写的文字。
她用文字梳理了横跨7年的极简人生,文章开头写了条声明:对于极简,我不仅做到了“精简”,更是做到了许多人标准里的极端。
但哪怕是带着这样的预期心理看完,我依旧全程瞠目结舌。
就像是一局十分解压的消除游戏。原本一间普通的出租屋,先是消除了杂乱,又没有了琐碎的家具,最后连床也消失了。她还在践行精神极简,删掉了无效的社交关系,注销了大部分社媒账号。与此同时,她的头发也越来越短,丢掉了裙子和化妆品,常穿一件钓鱼马甲,把整个城市当作自己的活动室。
搬家的时候,一个背包和一个购物袋,就装下了Chan的全部家当。
我想知道她如此做的原因,于是,我添加到了一个昵称空白、朋友圈空白、头像也是白底简笔画的极简微信。
我们断断续续聊了多次,与文字里流露出的冷峻理性不同,Chan很爱笑,笑声爽朗,又带着些南方女孩温吞的腔调。
我问她怎么能做到精简朋友,毕竟在大多数人的既有概念里,人是群居动物,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。更何况身处一个人情社会,“托关系”“找人脉”已经成了某种标配。
Chan却告诉我:让人不适的、无用的、冗余的人际关系,跟坏了的数据线、喝干的空瓶子、用过的纸巾没有区别,扔就是了。
再回头看那个空空荡荡的房间,在极简的标签之外,它还盛下了一个女孩的动荡与不安,以及更多的自由。
以下是Chan的讲述。


那一年,26岁的我终于下定决心,甩掉交往一年的男友。但我没想到的是,这事会让我妈勃然大怒,冲我怒骂:“你出去卖都不值钱。”
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,我和我妈在桂林租房生活。房子只有一个卧室,我和她睡在一张床上,每天对着彼此的脚入睡。我妈还是个极繁主义者,去海边玩就要捡贝壳回家,去河边也是,不带块石头她就觉得自己亏了,她喜欢喝茶,茶宠就买了不下十只。
大学毕业后,我在教培机构工作,收入很稳定,月薪三四千块,稳定的穷。
为了省房租,我始终没有搬出去住,但我妈已经迫不及待想赶我走了——从我毕业后,她就开始催我结婚。虽然我压力很大,却也积极配合,我同样希望婚姻能够帮助我逃离这个逼仄的环境。
母亲居住的环境
25岁那年,我和相亲认识的男生开始交往,我妈对此十分满意,连我的嫁妆都准备好了。所以即便分手时,我已经做好会被她训斥的准备,依旧不敢想象,她会用如此难听的话辱骂我。
那一刻,我只有一个想法:我要搬离这个屋子,我要离开她。
那是间一居室,房子不大,进门就是床,靠墙放着张书桌,厨房里热水器、抽油烟机这些电器都有配备。我对独居生活充满期待,尽可能想布置好人生中第一个小家。
我在房间里贴了很多装饰性的灯带,买了可变换颜色的台灯,连垃圾桶都精心挑选,斥99块钱“巨资”购入。后来算下来,购买生活用品的费用加上房租,已经占据我全部收入的80%,再加上吃饭,几乎存不下钱。

这样的生活过了两个月,东西也买得差不多了,我的人生非但没有被填满的幸福感,反而更加空虚。
就在那段时间,我关注到极简小组,看了一些帖子和相关的文艺作品,主动去找了国内外的纪录片。
这里不得不提到一本书,佐佐木典士所著的《我决定简单地生活》。我不看纸质书,一般会在拖地时听电子书,这本书就像一本工具书,直截了当地教我,要从什么东西扔起。也是在这本书里,提到了311东日本地震——导致福岛核泄漏的那次大地震。地震发生时,囤积的杂物倒下来堵住门,很多人因此丧生。
听完这一段,我立刻去搜了相关的纪录片。真实的影像更让人触目惊心,我至今仍记得一件事。地震后,日本政府预测到会有海啸,为居民们广播预警,一个男人开车去他父母家里,劝父母快点逃生,父母说不着急,先收拾一下行李。男人虽然不放心,还是带着自己的妻儿先行离开了,他以为父母会紧随其后,但海啸突然来了。
男人的行车记录仪里保留了他与父母的最后一面,两个老人正在整理东西。这个画面长久地停留在我脑海中,让我有了更强烈的极简想法。
我不想当那个地震时东西会堵住门跑不出去的人,我也不想当那个海啸来了还要收拾包袱才能跑的人。

我从很明显的“垃圾”扔起:断了的数据线,从公司薅来的文件夹……这些没有损失我个人经济价值的物品,扔了也不可惜。
后来慢慢发现,极简的能力是可以训练的,扔东西的阈值也会提高。若是将“功能性”作为判断物品是否必需的标准,会发现很多东西真的可有可无。
有时在扔了某件东西后,某个时刻也会想到,这个东西原来我有,现在如果它也在就好了,但下一秒就会立刻想到一个新的替代方案,或者一个新的解法。举个例子,我之前会用文件夹固定文件,后来我直接把几张A4纸折一个小三角形也能固定起来。
舍弃是一切的开始,践行极简主义六个月后,我扔掉了装饰画,空气净化器,毫无用处的装饰灯带,那些繁琐的、无用的东西消失在我的生命里,整个房间也变得干净清爽。
舍弃的缘由发生在部门聚餐那天。领导挨个劝酒,我打死不喝,饭吃到中途,我说我想走了。
在我的视角里,就在我说离开时,我那个醉酒的领导,狠狠地,朝我胳膊甩了一巴掌,对我说,你又不喝我的酒,又要提前离场,你是在驳我的面子。
我强忍着没有发作,走出酒店,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。有点可笑,虽然我对我妈没有什么期待,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,还是向她倾诉我的愤怒和委屈。
我讲完前因后果,我妈对我说:“一定是你有问题,所以别人才会打你。”我瞬间意识到,这个环境有“毒”。我妈有“毒”,部门领导更“毒”,我要远离他们。
回家后,我给领导发了一个微信。我在微信里写:XX老师,您打我那一巴掌,我实在受不了,我觉得是很大的冒犯。他给我道了个小歉。第二天,我就拿着这个聊天记录——聊天记录里他承认了打我这件事,我在校区里把离职相关的同事都找了一遍,说自己想要离职。
当天,我直接到了竞品公司,先找到HR首谈,HR首谈通过后,我和校长聊了半天,进行了试讲课,当即就确认了入职。新的培训学校在不同城市都有校区,我和校长说:“我在桂林可能待不久,如果这一年,你觉得我的表现不错的话,我希望你能够帮我跳到某个城市。”他同意了。
一个月后,走完该有的离职程序后,我入职了新学校。就这样,2020年,我顺理成章搬到了新的城市。
跨城搬家比我想象得还要简单。搬家当天,我花费了两个小时打包行李,和房东做好交接,然后带着我的全部行李——一个行李箱和一个双肩包,乘高铁离开了桂林。
像是一次简单的出游,但我心里知道,我正在斩断与这个城市的联系,我不会再回头了。

跨城搬家两个月前

桂林气候潮湿,一到梅雨季,房东配置的复合板家具就会发霉。
这些家具更是蟑螂的安乐窝,我最讨厌就是这种动物,看到就一定要处理掉。而且每次看到那个角落,想起蟑螂在这里待过,我都得恶心一个星期!
更何况,除了让我不断地定期擦拭以外,这些家具对我来说,也没有实际的用处。
在桂林生活的时候,我就在想能不能不要这些木板,这次要开始新的生活,我索性租了间纯空房。新城市的这间房里,房东给配了空调、洗衣机和热水器,除此之外,再无别的家具或者家电。
刚入住新城市时
入住之初,我添置了一个床垫用来睡觉,但床垫实在沉重,不方便搬弄,我就换成了竹板床。但梅雨季的到来,让我不得不再次放弃同样会发霉的竹板床,这次,我干脆只买了块海绵垫。
一块海绵垫使用半年后中间开始塌陷,我再把床垫裁开,把不塌的地方换到中间。这样算下来,80块钱的海绵垫能用一年。夏天,我直接睡在海绵垫上,或者把冬天的被子垫在身下。到冬天,我就将被子对折,用晾衣夹封边,做一个自制的“信封睡袋”,防风又保暖。
本来搬家的时候,我还备了一口锅,后来发现这个锅的使用频率实在有些低,我干脆把锅扔了,想找家社区食堂。当时在小区附近,有一对母女开的饭店正好开业,我去吃了两顿饭后,当即决定要在这家店办一个年费会员。
饭菜很便宜,两荤一素只要13块钱。衡量了食材调料价格,买菜、备菜、烹饪、收尾、清洁的时间成本以及餐具厨具的购物成本之后,发现比我自己做饭要划算得多。
使用床垫时

搬到新的城市后,我还做了更进一步的尝试:外表上的“极简”。
从2020年开始,我尝试脱掉束身衣。前前后后试验了多次后,最后选定了钓鱼马甲当我的夏季常服。与此同时,我开始丢掉化妆品、裙子、长发等社会刻板印象中的女性符号。
到2021年,我的固定穿着就是短裤、T恤,外罩一个钓鱼马甲。钓鱼马甲有很多口袋,我出门时连包都不需要了,什么东西都往口袋里装。我当时的领导同事也不怎么在意这些事情,只觉得我的服装风格变了。
而当我剃了一个很短的头发,穿得看似比较随意,去接触学生家长时,他们反而更信服我了。越接近他们心目中男性的打扮,他们越觉得这个女老师是教学能力突出的,就这么搞笑。
事实上,对我而言,短发可以极简掉一系列连锁事物:不用吹风机了,毛巾一擦就干;不用梳子了,手指整理就行;不用洗发水了,直接用沐浴露替代……另外,短发无形中加强了我的安全感,我能想到的还有,当我与人近身搏斗时,我最大的弱点也随之消失,没有人可以拽着我的头发,在地上拖拽了。
2021年的Chan
2022年,我抓住每个能出门的日子,穿着拖鞋,在整个城市徒步。整个城市都是我家的活动室,餐馆是我家的餐厅,电影院就是影音室。
培训机构的工作比人们想象中还要轻松一些,学生在学校上课的时间,就是我的休息时间。有一段时间,我的爱好是周一去看早场电影,电影是什么无所谓,我享受这种花一张电影票的钱就能包场的感觉。
2022年的Chan
2023年时,我干脆剃了一个光头。我在帖子里写了这件事,还有网友评论问我,这样的发型会不会被歧视。我回复了很多与我讨论极简主义的人,没有回复她。
“歧视”这个词,是她过度想象了她在别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我们可能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,但也不过两分钟,他们聊完你的八卦,也就过去了。
当她想象这个所谓的歧视时,更是在以一个外部凝视的眼光在观察自己,而不是从自己的心底,去思考到底想不想要这样的外表,这样的生活。

2020年时,突然有了大量时间自己待在家里,我的极简生活也从物质极简,迈向精神精简。
由于厌恶越发尖锐的互联网环境,我注销了大多数社媒平台的账号,只留下了联络用的微信。与此同时,我也主动退出了很多同学群,删掉了很多无效的社交关系。
出于工作原因,我一直有两个微信号。2021年,当我把私人微信的好友清理得差不多后,我就把私人微信注销了。除了个别转移到工作微信上的好友,其他人也都随微信号一起被注销了。从他们的视角看,我这个人也是直接消失了,号都“炸”了。

2021年的Chan
事实上,早在我没听说过极简主义之前,我就已经退出了所谓的同学群。也没有特别的原因,就是在某个时刻,我突然意识到,这些人我不再需要了。本来就是一群随机的人,分配到了一个随机的教室,随意地度过了几年时间,毕业了也就淡了,其实很正常。
我有几个从初中就一起玩的朋友,每年都约着聚会,我们还有个小群。但即便有十几年的交情,平时的聊天也就是更新一下近况。时间让我们面目全非,这种关系对我毫无益处,2021年,我也退出了这个群。
现在这个社会,断联真的太简单了。看似十几年的朋友,我们的联系也只有微信好友那一栏。“删除联系人”的按钮点下去,这个人在你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上全部都能消失。
而且我删人的点,可能很多人看来都是小事,忍一忍就过去了,但我忍不了。
比如,当年我甩掉前任后,和一个朋友倾诉了这件事,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她能安慰我,告诉我一个人也能生活得很愉快。我还给自己打气说,没事,我能找到更好的。但她回了我一句:“就凭你?”
我当时就很生气,既然你是我的朋友,你不是应该站在我这一边,狠狠把那个男人骂一顿吗?我立马把她删掉了。
当然,我知道很多人是无法割舍这些感情的,觉得自己的沉没成本很高,已经交往了十几年的朋友,付出的时间、精力都不可挽回。像这类人,可能面对亏损的股票,都无法割肉离场,但我是可以做到的。我会直视自己的沉没成本,如果它亏损了,我一定会及时割肉。
我认为,绝交、删除联系方式、屏蔽无效信息本质上就是扔东西。让我不适的、无用的、冗余的人际关系,跟坏了的数据线、喝干的空瓶子、用过的纸巾没有区别,扔就是了。
图源日剧《我的家里空无一物》
此外,物品是否可以被舍弃的标准,也是“现在”的自己是否需要。
不去想虚无缥缈的未来,我思考的是现在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用。若是未来我又需要这个物品,那我再把它买回来就可以了。物品是这样的,人也是这样。
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后,我就把前同事都删掉了。但补习班老师有个约定俗成的生意,就是自己租一个教室开课,利用手头的生源,赚全部的课时费。
在新公司任职后,我手头有一波生源,但我只是数学老师,需要英语老师给我辅助,我又没办法从现在任职的公司找人帮我,就把前公司一个比较熟的英语老师加回来了。她也很惊讶,她知道我把她删了。我很明确地跟她说,我加你回来,是想跟你合作,希望你来拓展一下另外一个科目。她很爽快地同意了。
图源日剧《我的家里空无一物》
当然,我也理解有些人不舍得丢掉这些人情世故,同样,也会有人不甘心丢掉那些承载着过去回忆的物品:泛黄的旧照片,朋友送的纪念物、学生时代的课外书等等。
十几岁的时候,我有了自己的数码相机。当时,我就把一些学习笔记、童年的玩偶、已经过塑的老照片都翻拍了一遍,这些记忆都储存在相机的存储卡里。
初中的时候,我狂热地喜欢着林俊杰,再加上我在学校也算是小有名气,可以说整个年级都知道我在追星。所以过生日时,朋友们几乎都会送我林俊杰的周边。后来不再喜欢他后,我就很果断地把这些东西扔掉了。
Chan曾经跨国看音乐节和演唱会的票根
均电子留存后就扔掉
2014年,我又开始追日本女团,为她们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。她们每次开演唱会都有一版独特设计的应援毛巾,我一直很珍惜,这块毛巾背后也是我们那群志同道合的追星小伙伴的共同记忆。
2019年,还在追女团的Chan
2021年后,我的评判标准变了,不再喜欢这些穿着高跟鞋用力跳舞的女爱豆。应援毛巾先是成为我的枕巾、后来变成浴巾,最后被用到泛黄,我也扔掉了。
后来,那些储存记忆的储存卡因为格式错误,无法再被电脑读取,当时还有些遗憾。搬了几次家,这些记忆也不知道丢哪里去了,不过倒也没什么遗憾了。
人的记忆是有限的,那些重要的东西会一直记得,那些忘记的东西,说明也不是那么重要。相比于实物所触发的记忆,可能留在脑海中的记忆更加珍贵吧。
在语言学校毕业时,同学送给Chan的手写信
也是拍照后再扔掉
2023年,我决定出国留学,非常迅速地制定了接下来的规划。
入学语言学校,辞职,雅思出分,确定目标学校、专业,一年后,我到了新西兰。
出国前,一个小背包和一个购物袋就装下了我的全部家当。塑料袋里是我没用完的卫生纸和夏季衣服等,小背包里是我的证件和电子设备,其他东西都被我送给了相熟的小区回收阿姨。
出国当天的房子和全部行李
如今,极简生活已经刻入我的生活基因,成为下意识的行为。有时课业压力一大,我就想扔东西,比如电脑C盘还剩50G的内存也不行,我得清理到还剩100G才能开始干活。
我和人合租,如果住得不舒服我就随时搬家,不会忍受,也无需内耗。我不需要特别多的朋友,现在和我一起做作业的同学,就是我现阶段的朋友,我们在毫无保留地分享各自在之前领域的专业知识,想要为这个项目出一份力。
当我们做完这个项目,这些人如果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的话,就散了吧。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,有利则合,无利则走,很正常。
前不久我清理网盘,看到自己这些年来的照片,表达欲突如其来,就又下载了社交媒体,写了那篇帖子。
我不会强求别人和我有所谓的“灵魂契合”,我知道,不可能有这样的人,非要有的话,这个人也只会是我自己。我才是最认同我的观点,最理解我的处境,最能同情我的经历的人,至于其他人,我也无所谓和他们深交。
在某个阶段、某个话题、某件叙事里,找到一个差不多合拍的人就足够了,在人生的全部叙事里,我似乎只想、也只能照顾好我自己。
由于时差,我这边已经凌晨,明天我计划去海边和图书馆逛逛,你想在这些时间和我聊天都可以,晚安。
如今的Chan
南半球春天来临,Chan又剃了个寸头
*除特殊标注外,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;首图来源于电视剧《我的家里空无一物》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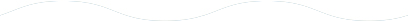



没有回复内容